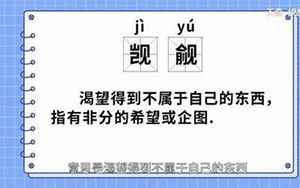司徒非(司徒非凡个人资料)
“中国纪录片之父”司徒兆敦去世,享年85岁
8月31日,据多位知情人士证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于8月31日凌晨去世,享年85岁。
司徒兆敦。图源“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微信公众号。
司徒兆敦,曾用笔名佐楠、梁梧舞等。1938年11月,他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开平赤坎,1951年随家人移居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留校任教。1980年6月入党。1997年9月,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金烛奖”。2016年07月,被中国电视纪录片学院奖授予“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杰出贡献奖”。2016年7月,被中法纪录片双年展授予德高望重的电影艺术家“终身成就奖”。
司徒兆敦。图源“青岛电影学院”微信公众号。
司徒兆敦曾拍摄电影《竹》《青山夕照》《父子婚事》;电视纪录片《路》《环境艺术》《光辉的历程》《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编著有《世界影坛佳话》等著作。退休后,他担任青岛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导演系主任,继续组织从事教学活动。
《父子婚事》《青山夕照》海报
司徒兆敦是中国电影界最受人尊敬的泰斗之一,他致力于纪录片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司徒先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的班主任,黄金“第五代”的伯乐。可谓是高徒遍天下,像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著名导演都师从于他。作为纪录片师者,他毫无保留地、热情地教导很多青年导演、学生创作纪录片,杨荔钠、张经纬等无数人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和鼓励。
司徒先生曾在采访中谦称自己“很有幸带了第五代”,回忆起第一次跟他们讲话时,他说,“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苏联那套东西,我们是从《战舰波将金号》起步的。经过这么多年了,电影怎么样了,我们完全不了解,对西方电影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敢说教你们,但是我有个优势,因为我父亲是管电影的,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大量的影片,对第五代这批学生的能力,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们人生态度、生活阅历,他们都有,这是现在的很多学生没法比的。我说那我们就一起看电影,看了大量的电影,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从这开始起步,因为商业电影我教不了,那个时候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社会, 对商业社会完全不了解,也不懂。”
除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司徒兆敦的家族历史更加令人侧目。
司徒兆敦的家族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华侨世家。爷爷司徒盛赞是北美华侨领袖、元老。司徒兆敦的父亲司徒慧敏,是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电影人、地下党。因为父亲地下党的特殊身份,司徒兆敦从小就见惯了“大场面”。
正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司徒兆敦一家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68年,司徒兆敦因卷入“二流堂”和“上海藏书楼”事件被捕,那一年,他30岁,之后的五年,他在监狱中度过。
有着不同凡响的家族历史,几经时代命运的影响,司徒兆敦依然塑造出朴实无华刚正不阿的性格。
在父亲的影响下,司徒兆敦自小就爱上电影。他在电影厂是从做杂活一步步做起来的。他自称,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的“电影厂的孩子”。
在司徒兆敦撰写的《司徒兆敦谈纪录电影〈演员〉:“真实即美”的审美观》一文中,他笔触犀利地抨击现实亦真诚地触及心灵。
“看《演员》,于蓝、于洋、秦怡这‘二十二大’的代表们,他们一直在强调演员不能只追求表面,要深入到角色的灵魂深处,只有深入生活,经过艰苦的努力,从思想到行为磨练自己,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才能塑造好人物,没有捷径……在那个年代,演员不论大小,角色不管正反,都是庄重的,有尊严的工作。我长时间在拍摄现场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它让我永远怀念。”
教书育人,司徒兆敦可谓没有任何架子,总与学生平起平坐来谈,一起研究电影。
在教学中,司徒兆顿会建议学生扎根自己熟悉的精神土壤,从本土中寻找创作根本,他一直认为,“到西方去学,你其他都可以学,电影你学不了。学完了你也不能在那生存,这是我的观念,学技术没关系,学录音没关系,学故事片创作,你就根本没法生存。 ”
对于电影创作,他一直是观点明确:“纪录片是大家的,不是你的专利。故事片专业的第一阶段必须学纪录片,第二阶段学故事电影。我越来越坚定一个观点,电影没什么了不得,电影就是一门技术,它必须跟其他学科知识结合,它才是有价值的。电影可以是各种样式,它也可以是商品,它也可以是政治宣传,它也可以是科学。”
因为剧情片烂片太多,司徒兆敦就强迫学生看纪录片,“不喜欢也得给我看,看够了纪录片你就发现,原来这些普通的脸是最漂亮的。”他强调,必须要从纪录片开始抓,通过纪录片的教育、渗透,转变我们的民族审美观。
有一位电影学院的学生说:“所有的老师看了我的片子后,都把我骂一顿,只有你教我如何将坏作品变成好作品。”
内蒙古籍青年导演呼可夫也是司徒兆敦的学生,毕业前夕,司徒兆敦曾私下问呼可夫毕业后的打算,他不假思索地表示要留在北京。司徒兆敦却建议他“不要留在北京,应该回到内蒙古,好好走一走看一看,等小有成就之后再回来”。
当时,呼可夫听从了司徒兆敦的建议,回到了内蒙古寻找发展方向。
呼可夫说:“我是在城市长大的蒙古族,从前对自己的民族没有概念,直到上大学的某一刻,我突然对自己的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看了大量历史文化类作品。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一直在拍消失的游牧文化,老师就让我回内蒙古扎根牧区,好好走走看看。如今才知道老师的建议是对的,因为我如果留在北京的话,现在也许就很难创作出好的作品了,也许就是拍拍广告什么的。”
从内心里希望学生可以成才,从长远的角度去规划学生的未来,司徒兆敦从没有疏忽或冷眼旁观过任何一个学生的问题。
2003年,司徒兆敦应邀来到纪录片导演魏时煜所任教的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这也成为了魏时煜制作的第一部纪录长片《记录之旅:原始档案》(A Piece of Heaven: Primary Documents)的契机。
《记录之旅:原始档案》海报
这部关于司徒兆敦的人物纪录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在香港授课、寻根的过程,魏时煜还以司徒兆敦为核心,延伸到了他周围的人。电影人父亲司徒慧敏、雕塑家弟弟司徒兆光、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和他的妻子罗丽丹等等。在这些珍贵和原始的影像片段里,我们得以见证时代的许多注脚。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作为师者的司徒兆敦是如何启蒙学生的,但同时,他更像一个朋友,和学生对话,激发他们对日常的思考。
“纪录片所记录的东西,常常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就是价值”,纪录片伊始,司徒兆敦在香港城市大学授课,他以中国电影先驱之一黎民伟拍摄的为例,介绍纪录片的价值是如何产生的。
在纪录片中,能看出司徒兆敦一生坚信的信仰和对电影深入骨髓的热爱。在举行告别派对时,司徒兆敦对着镜头说,“Louisa(魏时煜)以后会和这个摄像机结婚的”。活泼又风趣!
在北京电影学院,司徒兆敦说的一句话很有名:我可以原谅我说错话,因为我已经说了很多错话,但是,我不能原谅我说假话。他说:“什么是真事、真相、真理?这是我给学生必上的第一课,因为纪录片就要实事求是。”
敢说真话,认真做事,是司徒兆敦先生一生的本色。大先生一路走好!
我出殡那日 皇帝持剑拦路 神悲色哀 将她还我 我在棺材里看得清清楚楚
我出殡那日,褚奕持剑拦路,神悲色哀。
「将她还给我!」
我在棺材里看得清清楚楚。
1
我是姜国的笙宁公主,司徒芩妤。
三日前,我溺水身亡。
褚奕是我与皇帝巡游民间时,救下的流民。
他因战火失了记忆,但有些功夫,我便留他作侍卫。
得知我被萧贵妃推入荷塘,他一路赶来,却慢了一步,在我断气后一刻才推门。
举国哀鸣,他跪于灵堂前,不食不寝。
萧贵妃犯下大错,本该严惩,可皇帝却轻描淡写道:「戴罪之身,朕给她大举行葬,她就该感激涕零了。」
居然半点不罚。
我很气恼。
趁着夜深,我溜进萧贵妃寝宫,扼住她脖颈。
她猛然惊醒,见我惨白染血之面,骇得手足失措,失禁尿榻。
我森森道:「萧薇,我来索命了!」
她惊慌挣扎,难以出声。
我咬牙切齿:「黄泉寒凉,需你陪葬!」
片刻后,她晕了。
我收手起身,瞥一眼迷倒的侍婢,潇洒离去。
回到灵堂外,褚奕仍在。
须得小心。
所幸无人祭我,免去辗转躲避了。
我脱去鞋袜,赤足轻手轻脚经拐角,忽闻一声轻唤。
「芩妤。」
这声骇得我身形僵顿,屏呼止息。
褚奕梦呓一般,低哑道:「可想我陪葬?」
如哭如泣。
我的眼瞳微动。
晚蝉嘶鸣,白幔飘扬,他浑身落寞。
我忽然忆起,初见他之时。
2
那时我坐软轿中,于众人间瞥见他。
步伐失稳,跌跌撞撞,浑身是血。
见他身形摇晃,我指着他,对父皇道:「父皇,我要他!」
他扫我一眼,合眼倒下。
醒来后,见我第一句居然是:「多谢公主搭救,但草民一介武夫,担不起,恳请公主放过我。」
「褚侍卫切勿妄自菲薄啊。」
我道:「本公主鲜少出宫,对宫外奇闻趣事实在好奇,你讲给本公主听吧。」
他扫一眼我,不屑,转身跃上宫墙要逃。
一炷香后,被押回我跟前。
对上他怨愤的眼,我浅浅莞尔。
那时初雪,琼碎乱玉,赤墙白檐红梅,他一袭黑袍跪于雪中,墨发如瀑,剑眉浓目,如雕如琢。
我紧紧狐毛斗篷,不禁感叹:「褚侍卫生得真好看。」
3
后来褚奕再次出逃。
当他跳下宫墙时,墙角恭候多时的我起身拂裙。
他意外后退半步:「公主?!」
我道:「褚侍卫已至,出发吧!」
「去何处?」
「甑糕啊。」我让暗卫现身,疑问道,「难道褚侍卫此行不是为此?」
「……」
扫一眼众多暗卫,他蹙眉合眼:「是。」
我才莞尔。
还会审时度势啊少年。
那日他怀抱许多吃食,而我一手一串糖葫芦,蹦跶得欢快。
口含蜜饯,我将冰糖葫芦串呈他唇边。
「褚侍卫,你也吃。」
他偏头拒绝。
生于深宫,一时稀奇得很,日落才记起回宫。
暗卫将软轿置跟前时,一旁涌现许多乞丐。
不同于与皇帝出行那日的富足,他们个个瘦骨嶙峋,面黄肌瘦。
见我时,无力嘶吼着:「皇帝遗臭万年!」
「征扣民税不得好死!」
枯枝指节触碰我靴跟,惊得我紧抓褚奕衣袖。
褚奕只轻扫一眼,淡淡道:「公主莫慌,难民而已。」
我瞧着他:「难民而已?」
我一身锦珠玉缎,他们衣衫褴褛。
「褚侍卫。」我问他,「你说没的选与选不的,谁更可悲?」
「何处不同?」
我喃喃道:「同,也不同。」
4
晚夜后院,褚奕被我绑来赏月。
他道:「寒天雪地,何处见月?」
我回:「心中有月,时时见月。」
他冷嗤。
浅嗅院中梅香,我瞥一眼他腰间佩剑,紧紧斗篷。
确实冷。
我道:「我是宫婢之女。」
已转身的褚奕迈步。
我又道:「及笄之日,便是我前往金国和亲之时。」
他的步子一顿。
「和亲?」他回首看我,「你可是陛下心尖明珠。」
我问他:「往年你可曾听闻笙宁?」
褚奕蹙眉。
我是近几载被封号的。
萧薇立妃那夜,皇帝欢喜过头醉酒,意外临幸宫婢。
萧薇一直记恨,认为生母抢去她的气运。
我出生那日,生母气绝。
封号那日,我被宫婢从冷宫带出,途经萧薇寝宫墙外。
「还是陛下周全。」萧薇之声响起,「此举既露他慈父一面,保全我的公主,还能送走碍眼的孽种,一举三得。」
那日盛夏,我却手脚寒凉。
不过几载,举国皆知我笙宁公主,皆知我极尽宠爱。
皆叹皇帝慈父。
「褚奕,我没的选。」
我道:「这富贵灼得我生疼,那糖糕我也才尝过几回。」
泪红了眼,我忍着颤,道:「我只是想有个人在身后而已。」
雾浓雪落,片片飘散至他肩头。
那晚大雪,我见明月。
5
褚奕总不见人影。
我染上赌,总和各妃下注。
他回宫总先把我拽回寝宫。
「宫婢做什么吃的,为何会让你染赌?」
我道:「几日不见,褚侍卫愈发好看了。」
「不许打诨!」
我规矩坐榻间,乖巧道:「小赌怡情啊褚侍卫。」
遣去侍婢,我掏出些许珠宝,窃喜道:「这个可值好些,待我再去赢些,往后吃穿不愁啊褚侍卫。」
他直盯我。
我憨笑。
冬末风刺骨,身下宫墙掠过。
「褚侍卫。」我搂紧他脖颈,「抱紧些,我不踏实。」
他反手将我托至后背,让我趴得牢靠。
「公主。」他问我,「只馋甑糕我带便可,何必涉险出宫?」
我趴他肩头,笑道:「这赤墙生寒,不喜,那宫婢心杂,不喜,那膳食失味,不喜,唯有褚侍卫与甑糕,让我欢喜。」
褚奕静默刹那,叹息。
「此话万不能再说。」
将珠宝典当换银钱,分发难民。
褚奕随行眼眸几转,几番落我面颊,未言语。
回宫前,再不闻悲鸣。
褚奕不再反对我赌。
那日萧薇被我撞了轿。
晃了她的身,她下轿指着我就骂:「没家教的野丫头,竟敢冲撞本宫!丢了首饰本就心烦,你还眼瞎!」
我道:「白面朝天的,本公主以为见了纸人呢。」
「你胡说八道!」话虽如此,可萧薇依然抚上面颊,「来人,给这个没家教的野丫头掌嘴!」
宫婢挽袖迎上,我被压肩跪地。
宫婢抬手,却偏眼见了什么,下一刻惊慌退下。
萧薇不悦白眼,上轿离去。
及笄在即,我本意用被打一事,惹一惹皇帝不高兴,罚萧薇一罚,好趁机去她寝宫顺一把珠宝。怎知出此变故。
我意拂裙,手被牵起。
身形蔽光,入眼面貌几分眼熟。
「许久未见,性子还是如此。」
他朝服加身,身后随从众多,却为我俯身拂裙,细细掸尘。
他浅浅莞尔:「别来无恙,小妤。」
我不住后退,直至背抵褚奕胸膛,才闻自己迟疑声。
「三哥哥?!」
6
司徒钰烬,我的三皇兄。
八岁时,冷宫断粮,我与犬同寝同食。
酷暑犬食馊变,我又吐又拉三日,脱水脱相。
就当我眼帘生白,气至将绝时,门被推开。
司徒钰烬蹲我跟前,好奇地将我望着。
他稚声问我:「你是何人?」
宛记那日日光明媚,他的出现胜过曙光。
寝宫,褚奕松了剑柄。
「所以于你,他是恩人?」
「何止,若非他照拂,此刻我便是坯土了。」我道,「初经月事,还是他教的我。」
褚奕一愣。
「月事?!」他提了些声,「你说月事?!」
我点头,轻声道:「所幸那冷宫只我一人,污渍染了裙摆都不知——」
啪!
话至半只听一声响,抬眼寝宫不见了褚奕人影。
宫门余震,剩我茫然。
不过拿来新衣裳而已,他为何如此动怒?
褚奕又消失了。
我满心等他,司徒钰烬到来也未觉察。
「小妤。」
这一声骇得我一抖。
「为何闷闷不乐?」他至我身旁,温声道,「可说与兄长听?」
久别重逢,司徒钰烬眉目愈朗,褪尽稚气。
我往旁挪了挪,道:「皇兄还是离我远些,我是不祥之人。」
他肃起面,道:「兄长何时信这?」
倏尔,他又复温吞,道:「我还是喜你唤我三哥哥。」
在他满目期许中,我抿唇,默。
直至他眼中光如火熄消。
他微不可察地叹息。
「罢了,只要小妤欢喜,如何唤我都可以。」
几年前,他狂奔至寝宫。
「小妤!」他急慌慌牵住我的手,「倏忽赐你封号,以我对父皇的了解,父皇此举定有目的,我不能让你陷于危险,你快随我走!」
我回握他的手,应道:「好!」
我问他:「之后呢?」
他身形一顿。
我迟疑,复问:「随你出逃,之后呢?」
他犹疑着:「之后再想办法……」
那时别说他,连我自己都未曾料到此困境,压根无后手。
我可以选择与他莽撞出逃,不管不顾。
可他的母妃、至亲、族人无一例外都会受牵连。
理智警诫,他是唯一真心相待之人。
选不得。
「罢了。」
我松开他的手,道:「人生苦短,潇洒几载是几载。」
我道:「三哥哥,同与你奔赴未知相比,我选荣华。」
7
褚奕回宫时,我蜷榻上睡着了。
是甑糕香味将我唤醒的。
褚奕将热腾甑糕放我手中,这才解下腰间佩剑,拭去唇角星点血渍。
「想起今月事,会念这一口。」
温热从掌心延至心房,我却撇嘴道:「那日莫名动怒就走,几日不见人影,就拿这哄我?」
褚奕挑眉,竟伸手要将其拿回。
「不要就罢!」他嘟囔,「是不及司徒钰烬所备佳肴一分。」
我间甑糕举过头避开他,歪头问他:「所以你总在宫中偷瞧我?」
「……」
褚奕眼眸微转,面颊映红,却道:「胡言!」
「骗人!」
他撇嘴,不耐道:「信不信由你。」
见他转身要走,我眼疾手快抱他腰,紧紧锢着他。
「不许走!你这一走又不知几日才能见,你就仗着我寻不到你欺负我!」
褚奕僵着身,道:「你先放开我。」
「不放不放!放了你又不见了!」
他默片刻,轻叹息。
「明日带你出宫。」
宫外景象,大不以往。
难民难见,平和景象。
褚奕才将我放下,其一人指着我大喊:「公主!是笙宁公主!」
众人回首,纷纷将我俩包围。
声声道谢中,我看向褚奕。
「你做了什么?」
褚奕道:「你作甚我便作甚,那些你难得的珠宝我来取,你难达之处我来踏。」
我笑:「大盗!」
他的嘴角微扬:「皆奉公主之命。」
8
皇帝已筹备及笄大典。
宫婢来往忙碌,我独坐枯梅树下。
化雪时节,寒凉刺得骨生疼。
褚奕为我覆上毛裘,慵懒倚树。
「红梅已枯,殿中暖炉才暖身。」
我道:「不喜红梅,只叹白雪消逝无痕。」
褚奕偏了眸,顿了片刻,才道:「三月梨花遍地,胜过皑皑白雪,待至三月,我带你去。」
「三月啊……」我喃喃道,「可我二月就及笄了。」
寒风凛冽,褚奕蹙眉。
我问他:「褚侍卫,你说金国有梨花吗?」
他合上眼。
我问他:「褚侍卫,民众会因我及笄喜悦吗?」
他缄默。
我絮絮叨叨问他,他全不应。
「小妤!」
司徒钰烬踏入后院,还未换下朝服。
与褚奕四目相对,他的步伐僵顿。
「寒冬已去,兄长寻了世外桃源,定能阻绝凡俗!」司徒钰烬伸手,问我,「可愿同往?」
发丝拂经他精雕玉冠,拂经他几分慌张的面颊。
此景恰如数载前,他要带我出逃那刻。
我弯唇,问他:「可是父皇宣了和亲一事?」
司徒钰烬肃然。
我问:「皇兄本为储君,此举不怕功亏一篑?」
「不怕!」他不曾犹疑半分,道,「小妤胜过一切荣华!」
如此果绝,震得我心房刺痛。
我回首与褚奕相对一眼。
「皇兄怎么上朝还醉了酒。」我起身至褚奕身旁,笑道,「此事莫要让父皇知晓,他会恼的。」
司徒钰烬紧眉!
「小妤!」
「皇兄。」
我阻断他未出口的话,隐入褚奕身后。道:「褚奕在旁,万千险阻我都不怕。」
「芩妤!听话!」司徒钰烬伸出手,言语卑微,「听话……」
眉目坚定,掌心宽厚。
我身侧的指尖动了动。
那年出逃未果,他母妃曾找过我。
「我不知你下了何种,能让烬儿如此迷恋,但我也不阻你俩往来。身为人母,我只求你,万事念一分他的好。」
那晚深夜,他母妃一身素衣,褪去嫔妃身架。
她道:「深宫无情,你最是透彻。」
她求:「我希望他永远安康。」
枝头枯梅摇晃,我背身相对,抓皱身侧裙摆。
「褚奕,送客。」
9
典礼前夜,褚奕带我偷了萧薇珠冠。
烛火间,铜镜前,他动作笨拙,却轻柔地将珠冠戴我发髻。
红绒玉珠,浮翠流丹,珠链相扣。
褚奕颔首,眼含缱绻,指尖蹭过我耳边。
「公主真好看。」
我莞尔,调笑道:「与褚侍卫般配吗?」
橙光暖色中,他一愣。
「……公、公主怎胡言乱语了……哪有公主下配侍从的。」
他握拳掩唇轻咳,偏头移目,耳鬓却赤粉。
许久,隐约听他低应。
「承幸。」
典礼当日,宫中热闹非凡。
簇拥间,我见萧薇胭脂掩不住的青脸。
皇后雍容华贵,品行美貌过她大半。
宫墙外整装待发的人马挡住民众,我登上城墙,迎着如风般的贺语。
「公主。」褚奕对我耳语,「车马已备,待晚宴一开,众臣群涌时,可脱身。」
我点头。
他默了片刻,又道:「三皇子已知此事,届时会替公主除阻开路。」
我微抬眼睑,远眺红幔帐延绵数里。
「褚侍卫,听闻城外近境温暖,花会早开。」
他看着我。
「时辰尚早。」我指着远方,笑道,「褚侍卫,我想要一枝梨花。」
他果断拒绝:「不可。」
我撇嘴,嗔怪道:「我司徒芩妤活一世,想要个贺礼都不行?罢了罢了,也不知往后还能否与你一同,见一见那梨花……」
「且过今日。」
「可我就今日最想要!」
褚奕面露难色。
「你……非要不可?」
我歪头看他,问他:「何曾骗你?」
他抿唇片刻,陷入两难。
最后,认命一般。
「此行尚久,你乖些,晚宴前我来接你。」
我欣然点头。
注视褚奕远去,暗卫悉数跟上。
我渐失去了笑意。
「司徒芩妤!」
萧薇愤愤然赶来,柳眉倒竖。
「是不是你窃了本宫的珠冠,让本宫丢尽颜面!这宫中只有你胆大包天!」
我从袖中掏出颗珠子,问她:「你说这个?」
「你竟将它拆了?!那可是陛下赐本宫的!」
萧薇一见,瞪大了眼,伸手就要抢夺!
推搡吵闹引起瞩目,皇帝闻声而来。
司徒钰烬提襟昂首,举手投足沉稳悠然。
对上他视线,我弯了眉眼。
下一刻,我与萧薇,跌落护城河。
他慌忙伸手,跨步间跌了跌。
「小妤!」
10
金蝉脱壳,褪去旧形,方可重生。
待我从假死中回神,宫中已变天。
传闻萧薇因我滑胎,皇帝龙颜大怒,却念及情分,许我风光大葬。
原先怎不知萧薇有孕,分明是为脱骂名胡诌。
皇帝将慈父演至底,却嫌我晦气,禁人祭拜。
我问暗卫:「可确将褚奕拦住了?」
「是。」
我缓了缓神,又问:「三皇兄呢?」
「三皇子当日追您跳了河,陷入昏迷。」
我呼吸一滞。
额穴倏忽刺痛,如针似刀刮剜深骨,痛得我紧按命门,亦不得缓解。
初春河水刺骨,怕是落了病根。
11
晚风阵阵,拂起白幔,擦我灵碑。
旧忆抽身,我再迈步,下一刹颈边一凉。
「你是何人!」
就在我愣神间,他悄然而至,持剑抵我命脉。
我眨眼。
果然是逃不过他的。
「饶、饶命!」我颤着嗓,道,「奴婢是公主新选的侍婢,颖颖。」
他抬剑勾住我下颌,道:「转过身来。」
我照做,有些忐忑。
四目相对,他眼角泛红,惫态尽显。
见我面上血渍,他面露疑色:「侍婢?」
我扑通跪下,边磕头边解释:「陛下禁止祭拜公主,奴婢实在痛心,这才出此下策吓跑守卫,还求大人高抬贵手,饶奴婢一命!」
褚奕默了片刻,收了剑。
还好早些时候提过颖颖此人,此刻易容破嗓,他不可能识破。
褚奕背身而对,面朝灵堂,问我:「公主玉殒,你不逃?」
我摇头,道:「公主生前待奴婢极好,榻前曾嘱咐奴婢,待大人归来,紧随其后。」
「跟我?大势已去,跟我何用?」
瞧他萎靡不振,我认真道:「公主让奴婢嫁与大人。」
褚奕眉头一动,拔剑相对!
他愠怒道:「公主灵堂前,你竟敢胡言乱语,无中生有!」
此举骇得我后跌,掌心撑地后退一步。
我惊慌道:「公主曾言大人品行极佳,却不得善用,倍加惋惜。也曾言待大人回宫,就做主将奴婢赐婚大人。」
我道:「奴婢所言句句属实,不敢欺瞒大人!」
他握着剑,腕间颤了颤。
「……这确是她的作风。」
指节松懈,掌中剑叮当落地。
他失神喃喃:「她竟是这般。」
瞧见他袖间半露之物,我一怔。
那是一枝枯萎梨花。
12
天明宫中便热闹起来。
听闻萧贵妃萧薇顾不得梳妆,跌跌撞撞投入皇帝怀抱,哭得梨花带雨,句句不离昨夜遭遇。
皇帝心疼不已,早朝都让她跟着。
当真宠爱。
彼时褚奕跪于灵堂前,而我端来食物。
「褚大人,好歹进些膳食。」
他垂着眼,问我:「是公主之命?」
指萧贵妃一事。
我摇头,盘腿坐他身旁。
不料未坐稳当,褚奕一声低喝:「放肆!须与我同跪!」
这脾性胜过初见啊。
我撇嘴,照做间,嘟囔道:「是,夫君。」
有朝一日,竟要跪拜自己灵堂,荒谬啊荒谬。
褚奕厉声道:「不许唤我夫君!」
我点头,弱弱道:「遵命,夫君。」
「……」
咣的一声,宫门忽起声响!
我俩回首,只见一群道士来势汹汹,包围灵堂。
褚奕站起将我护在身后,才见皇帝和萧薇身影。
萧薇扭着腰,指着我的灵牌,骂道:「该死的!居然还敢阴魂不散,看本宫今日让你魂飞魄散!」
皇帝轻揉她肩头,目光扫过我俩。
褚奕未动,而我捂嘴缩他身后。
道士开始做法,皇帝盯着我俩若有所思。
片刻后,他道:「朕见你俩忠心耿耿,既然如此,往后此宫就赏赐于尔等,也算为她善后了。」
听听,囚禁说得多好听。
道士们围绕棺材舞动符纸,一屁股将我俩挤出去。
见他们将符纸贴于棺材,木剑插缝,我心中咯噔一下,猛察不妙!
我急忙要出声制止,却听身旁更有焦急者!
「不可!」
褚奕飞身而去,踩住棺盖。
他怒道:「不可惊扰逝者!」
我挠挠面颊。
少年,你脚踏之处,该是我脑袋位置。
13
皇帝怒道:「大胆!朕怜悯她,她却纠缠爱妃,阴魂不散,此等罪人就该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滚开!」
褚奕不肯让,还拔出剑来。
皇帝怒火中烧,挥袖下令!
「来人,将他拿下!」
宫兵鱼贯而入,蜂拥而上!
眼看着褚奕身影在我棺材盖上起起落落,我旁观。
万一把我棺材蹦塌了怎么办?
好贵呢。
杂乱之际,萧薇凑近大喊:「但凡与司徒芩妤有关联者,统统杀无赦!」
我惊了!
皇帝不及你狠啊。
宫兵包围,我崩溃模样跌坐,盯着萧薇,大喊大叫:「公主?!您怎么回来了?!」
闻声萧薇小脸煞白,不敢动弹!
「你这贱婢胡说八道什么!」皇帝恼怒,一把揽过萧薇,对宫卫道:「鬼迷心窍撞了邪,来人,杀了她!」
我立马爬起跑向褚奕,大喊:「褚奕救命!」
褚奕稳当落地,将我护于身后。
眼见宫兵围上来,我立马跪倒棺材旁,挤出泪哭喊:「公主!上天不公,竟让您如此玉殒!」
话音一落,堂外忽起狂风,携卷角落堆积枯叶肆虐。
变故让堂外皇帝一愣。
萧薇惊恐:「陛、陛下,您看,臣妾所言句句属实!」
「闭嘴!」
早知变天,我擦着泪,哭得极其投入。
褚奕未收剑,垂眉抿唇。
落叶平息时,宫门外来了位侍卫。
侍卫呈上一卷血书,道:「陛下,民众血书上奏,求陛下重惩萧贵妃,还笙宁公主公道。」
皇帝大怒:「一群乌合之众!搭理他们做什么!」
拭去泪花,我才看清那侍卫是司徒钰烬属下荆离。
这步怎是他替我?
他醒了吗?
14
和亲公主及笄日溺亡,可金国却不依不饶。
书信传来:无和亲者,起烽火。
大晋眼下可只有萧薇之女了。
萧薇夜夜哭诉皇帝不疼她娘俩,皇帝被烦得止步后宫。
而我夜夜伴着哭声入睡,极其安稳。
出殡前夜,灵堂涌入一队人马。
深眠惊醒,褚奕已被包围。
皇帝禁令还能堂而皇之破禁,来人身份疑云惹我心慌。
顾不得外袍,我只着里衣赤足奔向褚奕,见他安然无恙才放心。
软轿入堂,褚奕伸手将我护在身后。
轿中人道:「明明全心信你,你为何辜负?」
我一愣。
帘帐掩住身影,堂中只有司徒钰烬低嗓沉息。
「那的模样,我当真以为你能护住她,还派死士暗中保护,可你就是如此护她的?」
语塞须臾,是他咽下咳嗽。
司徒钰烬道:「褚奕,你当如何赎罪?」
话音一落,侍卫荆离一脚踢得褚奕生生跪地。
褚奕竟对司徒钰烬不设防?!
「三皇子!」我扑通跪下,急道,「此事纯属意外,人各有命,怪不得褚奕的!」
司徒钰烬话语危险:「你此言是小妤命该如此?」
我语噎。
谁人自咒命该如此啊。
不等我编,荆离忽一掌重击褚奕后背,褚奕身形不稳,口吐鲜血。
当我脑中空白之际,又几鞭鞭他后背,黑袍乍破,渗出血液。
「褚奕!」
我跪行向他,却被荆离强扯一旁,压住臂膀,动弹不得。
眨眼间又是几鞭,褚奕咬唇硬扛,我却破了防。
眼见褚奕唇角落血,我挣扎大喊:「司徒钰烬,公主泉下若知此事,定会怨恨你的!」
司徒钰烬眸色异闪,视线触及身旁棺材。
施暴兵卫止了动作。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06-13八字女命童子(如何化解童子命)
- 06-28耳朵后面有痣代表什么(耳后有痣代表什么)
- 06-24下巴底下有痣(下巴底下长痣代表什么)
- 07-13夫妻宫有痣(夫妻宫长痣代表什么)
- 07-05左脸有痣(左脸有痣代表什么)
- 06-26七杀在夫妻宫(七杀在夫妻宫是什么意思)
- 07-12右眼角有痣(右眼角有痣代表着什么)
- 06-20批八字清娟(清娟盲派命理逐条细解)
- 07-04左耳长痣代表什么(探究左耳长痣的神秘意义)
- 07-06脑门有痣(额头上长痣代表什么)
痣相命理最新文章



- 09-30司徒非(司徒非凡个人资料)
- 09-30生肖38岁后运势(83年属猪人38岁以后运势如何)
- 09-30马微(法定代表人高管股东)
- 09-30冬月初十(冬月初十是什么星座?)
- 09-3073年属什么(73年属什么生肖 今年多大了)
- 09-30侯锋(侯锋个人简历)
- 09-301999年多少岁(1999年多少岁2023年)
- 09-30哪个星座运势最高女生(赢在最后的星座女)
- 09-30属土的饰品(属土的饰品都有哪些)
- 09-30沪深300指数基金排名(沪深300指数基金哪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