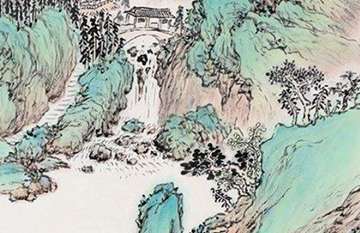梦见房子漏雨(梦见房子漏雨是什么意思,周公解梦原版)
真实故事三则,做梦梦见有人告诉我家里漏水了……
01山精
与水蟒鬼一样,这件事也是听我那个印尼工人说的。
他说在印尼爪哇,有一种山精,长得很像猴子,但是却双足直立,有自己的部落,但是族群不会太多。
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大脚怪,但他说没有那么高,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体格,但是力气大,移动迅速,没人能捉得到。
而且它们还能言语,爪哇常常有传说谁家的孩子和山精成了朋友。
一旦山精认定的朋友,就会常常帮助他,送些山货什么的。
不过山精几乎不跟成年人做朋友,可能对人有防备,不像小孩子单纯,容易满足。
在爪哇很多村子杀鸡,都会把鸡杂埋了或者烧了,
因为对山精来说,这些是美食,容易把他们引来。
为什么村民会惧怕山精到村子里来呢?
原来雄性山精非常好色,还可以在晚上幻化成男人,引诱村民的妻子。
有些村民很好奇,想看看山精是什么样子,于是就想办法吸引他们出来。
后来发现,比起鸡杂,烤乌鸦更让山精无法抵挡。
于是就有人在传说有山精出没的森林边缘,烤几只乌鸦,总能把一窝的山精引出来。
我就好奇了,那这样不是很容易设陷阱抓山精吗?
印尼工人说,人不是应该与自然和平相处吗?没事抓他们干嘛…而且山精也不是动物,像是山里凝结成的精怪,离开了山,估计可能会消散。
我觉得这种东西跟中国传说中的山魈差不多吧。
2、净地
这件事发生顺德,好多地方都人云亦云被说成乱葬岗,但有一个地方我很肯定曾经是乱葬岗。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那里曾经有颗木棉花树,树身很多人脸的轮廓,十分怪异,后来政府改造此地,将这颗树砍了,砍的时候,树流出来都是红色的汁。
改造前还安排人打斋等仪式,后来在旧址建了15层高的大厦,那时候算是挺威风的。
但建好每几年都会再净一次地的,净地的时候都会私下通知周围的居民,能不走就不要走那条路,
但为了避免引起恐慌,这件事也没有明确说为什么,都是口耳相传。
又一次朋友的妈妈不知情,带着年幼的儿子经过那里,
一回到家里儿子就好像发癫一样捉住床边的木栏不停摇,喊:“快放我出去啊!快放我出去啊!”
妈妈问他怎么了,但他就是没有反应,而且力度非常大。
妈妈当时吓倒了,马上叫人回来处理。
一五一十交待了事情,神婆话可能冲撞了,后来就把事情处理掉了。
但朋友告诉我,那段时间入夜会听到有人拉她家神台,拿香点的声音,所以有段时间我都不敢去她家。
还有一次那里净地,因为有亲戚就住在那块地对面,
那天我跟妈散步去亲戚家,我妈走时候再三叮嘱亲戚,明天十点到两点将门窗关好,阳台和门口放扫把,别人来拜访你都不要开,叫他迟点再过来。
3、漏水
十年前刚毕业出来工作,在阳江租房住,
有天阳春的亲戚电话我,让我过去谈一个朋友(相亲那样),然后住在亲戚家(老式商品房),
晚上见了一面那朋友,他忙手上工作说没空饮茶,让第二晚再约会。
就这样回到亲戚家冲凉睡觉,第二天天快亮时,我朦朦胧胧看到一个身穿褐色长袍的人和我说话,
说我阳江的出租房水龙头没有拧紧关水,让我早点坐车回去……
我摇摇晃晃头起来,感觉做了一场梦,但又很清晰,想了想会不是我发梦糊涂了,
于是和亲戚说我要赶回去看看,但晚上要会见“对象”,到底哪样重要,
我想了想不放心还是要赶回去。
当我回到出租房吓了一跳! 厕所爆水管水一直在流,应该流了一夜了,
和房东说了,他说看我刚出来打工没有什么钱,减了一点水费,记得那个月给了60元水费。
后来又和亲戚说起这事,是有穿长袍的人,她父亲,就是我们叫的啊公,那年代长袍装或中山装,但已经走了20年了。
甘宇绝境求生背后:水电站4人身亡,家属扯着头发哭,遗子问爸爸呢
从那座山林走出来后,甘宇做了好多次噩梦。梦里,他仿佛又回到了那片渺无人烟的山林,大声呼喊“救命”,等来的只有空荡荡的回声。
这名四川泸定县湾东水电站28岁的施工员,在9月5日泸定6.8级地震中,和同事罗永救助伤员、拉闸泄洪,错过逃生机会,绝境求生17天后才获救。
10月8日,他出院了,回到达州老家休养。他还是会想起地震那天,巨石从山上滚落,砸向在大坝上的人。十名工友侥幸逃生,四人被砸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其中就包括罗永的亲哥和好友。
更早前的9月28日,罗永一家一早从临时安置点出发,去给逝去的亲人做法事。一路上,他们很少开口。车静默开在山路间,沿途仍有些许塌方与滚石,更远处,滑坡后的山体裸露出一道道伤痕。
它如同横亘在幸存者心底刺眼却又鲜少提及的创伤。在这场地震中,遇难、逃离、留守、幸存,水电站里16个人的命运彼此交织,一个普通的抉择也变得性命攸关。
地震来临前
孙建红的不安感很早就有了。
32岁的他是一名焊工工人。8月29日,他带着6名工友,第一次来到湾东水电站。
这座2019年建成的水电站,位于四川贡嘎山东侧山脉的夹沟处,北接甘孜州泸定县,南邻雅安市石棉县,周围有45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
水电站大坝海拔1192米,坝体高25米,在两叉河下游筑坝取水,水顺着穿山隧洞、压力管道,引至下游河谷地带的厂房发电,厂房离大坝车程约一个半小时。
刚来第一天,孙建红就发现,大坝宿舍前方是河、后方是岩,离山体仅十米左右,像是卡在槽里。而且附近山体陡峭,山上树木不是很茂盛,是石头山。他担心,“滚个石头也要倒霉。”
因汛期河道涨水,冲毁了大坝护岸,宿舍楼随时有塌方危险,孙建红和工友过来打堡坎——在钢筋笼子里装满石头,焊死后用挖机码河沿上,保路保房。工期原定20余天。
工人们自己烧火做饭,晚上睡搭的工棚。孙建红原想把工棚搭到坝上,但坝上有时要过车,不方便,只好搭在大坝宿舍旁边。9月1日,他在宿舍墙角放了米和一块肉,连着三晚没被老鼠动过。他心里惴惴不安起来。
孙建红与甘宇所在公司同事的对话。受访者供图
9月4日,罗永招了3位工人帮忙搬运石头,他们是罗永的哥哥罗开清、侄儿杨刚和马正军。都是他在湾东村相熟的人,早上上工,下午散工后各自回家,一天工钱170元。
指导现场施工的,是施工员甘宇。他28岁,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比较斯文。相处几天,孙建红觉得甘宇待人和气。
甘宇住在厂房,每天早上开车到大坝,晚上再回去。他8月底刚请假回家给奶奶过生日,项目上缺人,被紧急叫了回来。
除甘宇外,平时驻守大坝的是3名水工,罗永、彭云军以及邓荣。他们两人一班,24小时轮班监控水位变化,及时拉闸泄洪。
罗永介绍,7-9月汛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有时半夜要清两三次渣——用机器把上游飘来的枯枝、树叶等杂物捞上来。“如果不发电的话,水就进得快,下大雨几小时能装满(注:指接近最高承载水位)。”
彭云军就经历过一次险情。8月的一个夜晚,雨下得大,他一夜没敢打瞌睡。守到天亮,水位基本平稳后,他骑摩托回家吃饭,没吃几口,不安心,又跑回大坝,一看水差几十公分就翻坝了。他慌忙把闸门一提,撒腿就跑,“差点都没有跑赢,他说把他吓惨了。”彭云军的弟弟彭荣强回忆说。
水工们平时吃住都在宿舍,一座离大坝没多远的两层小楼,监测水位的电脑也在里头。他们做两周休一周,春节也只能轮休一两天。
汛期之外,水工不用时刻提防水位、天气变化,工作轻松不少。但这份月薪3000、没有五险一金的工作,41岁的罗永用以负担两个孩子的读书开销有些吃力,好在他自家也种菜,能省些钱。轮班的两周里,他基本是煮个青菜、炒点腊肉,连吃三顿。没事做的话,他就搞搞卫生,连着把大坝的路也扫一扫。“有事干还是比较踏实。”
但对临时赶工的孙建红来说,宿舍里迟迟没有的老鼠,加上身处群山带来的压迫感,让他愈发有种不祥的预感,没干几天他就先走了,这个决定让他成了现场施工队中唯一一个躲过地震的人。
“山崩地裂的,不跑咋办?”
9月5日,一个平常的工作日。
中午吃完饭,6名焊工、一位挖机师傅刚刚开工干活。3名拉水泥的工人刚来到大坝,把车停好,换好衣服,准备下水泥。大坝下方的宿舍休息室里,水工彭云军和3名搬运工在烤火,甘宇和罗永在聊天。
12时52分,伴随着剧烈的震动,甘宇看到,休息室窗户玻璃顷刻间震碎,房间里的设备“全都炸了”,大家慌忙往外跑。
另一名焊工颜清华看到,“房子三面墙有些都被山上的石头打穿了。”
逃跑的时候,山上已经开始垮了,发出“哐哐哐”的滑坡声。一块石头砸向甘宇的后背,把他推到了休息室下方的坡上,他有些晕,马上爬起来往旁边开阔的平台跑,那边相对安全些。
眼镜掉了,近视500度的他,有些看不清。恍惚中,甘宇看到不远处,罗永搀扶着哥哥罗开清——他被落石击中,受了内伤,走不动。旁边有两个伤员:水工彭云军倒在被山石掩埋的休息室废墟中,浑身是血;搬运工杨刚半个身子被大石头压着,头窝在泥里,脚还在蹬。
其他在室外的工人,纷纷往外逃。山体垮塌后,一些闸门被封死,不走水,他们淌过河床,往对面跑。
“如果(石头)再滚下来,我们也救不了了。”甘宇尝试去搬压在杨刚身上的石头,太沉了,推不动。
跑在后面的颜清华见状,折返回去帮忙。挖机师傅帮他看着山上掉下的石头。颜清华试着搬杨刚身上的石头,搬不动,只能帮忙把受伤的彭云军就近抬到河边。后来,甘宇和罗永把他抬到更安全的平台上,回工棚找了床铺盖给他垫上。
很快,“山上又下了一大片石头”,颜清华顾不上了,也往河对面逃。
只剩下甘宇和罗永两人。
甘宇提议,马上上坝提闸。水电站用来发电的压力管道,垂直落差超700米,途经湾东村多处民房、农田。一旦水位翻坝,可能引发泥石流“把下面(的村庄)都冲了”。
罗永答应了。临走前,他让心口疼的大哥一定要坚持住。
上坝的混凝土路,早已垮塌,“路很悬,一直在滚石头”,罗永心头有些慌,手脚并用冲了两次才成功上坝,用柴油机发好电后,提上第一道闸。随后,他拉着甘宇一起上坝,提了第二道闸。
“假如他不提水闸,你采访的那些人就(可能)都不在了。”罗永的妻子杨秀清对记者回忆,地震后,压力管道一下爆了,水柱喷涌。“最多20分钟,我们边上的一片山都刮完了。”水停时,不少湾东村村民都难以置信,水电站居然还有人守在岗位上。
但在罗永提完闸门后,他的哥哥、工友都已断了气息。
眼睁睁看着工友离去,甘宇难过,却又无力。另一位搬运工马正军,地震后完全被山石掩埋,当场去世。
马正军生前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颜清华说,逃出去的10个人,往猛虎岗方向走——这是当时唯一的出路。这是一条老伐木路,一米多宽,常供村民放牛。因多处塌方,经常绕路翻山。2个走得快的,当晚先下山了。剩下8人到猛虎岗时天已经黑了,就在猛虎岗过了一夜,烧火取暖,天亮后继续下山,上午11点多抵达王岗坪。
孙建红看到,逃出来的工友们个个脸是花的,全身是泥,裤子、鞋子磨破了,手脚遍布擦伤。
他问,“咋不把甘宇和罗永带出来?”
工友们说,“那种情况,山崩地裂的,不跑咋办?”
“只有一瓶水,他还一直叫我喝”
滞留水电站的罗永和甘宇,在发电机机房里过夜。
两人认识一年多了,以前见面多是打个招呼,吹上几句,当晚气温降到10℃左右,他们没怎么睡觉,聊着彼此的家人,说要能活着出来,得换个安全点的工作。
9月6日,水电站周边山体塌方和滑坡依旧,两人决定撤离。厨房门口已被落石堵住,他们找不到吃的,只带了逃生绳、安全帽和一瓶山泉水。爬山消耗太大,仅有的一瓶水半天就喝光了。罗永说,甘宇体力差一些,爬山爬不动,“只有一瓶水,他还一直叫我喝,我都说我不渴”。
下午两三点,甘宇给单位领导发了定位,两人找了个空旷处。罗永爬到树上,把甘宇的白色短袖绑竹竿上,几小时间,一听到直升机过来的声音,就赶紧摇衣服,但树林太密,他们始终没被发现。
与此同时,甘宇拿着两人电量都不多的手机,在另一处信号稍好的地方等救援电话,但他只接到了罗永几个亲戚打来的电话,具置也说不清楚,为了省电,只能匆匆挂断。
山上有猕猴桃、野梨,八月瓜基本都被野猴吃光了,路上只发现了两个,罗永爬了十米高的树摘下来,给甘宇吃,自己没吃。“饿还是饿,但是还扛得住。”罗永也没什么胃口,亲人在地震中相继离世——地震发生不久,他就接到家里电话,他母亲被倒塌的房屋掩埋了。
傍晚时分,他们想钻木取火,使劲搓了干木头一二十分钟,手都搓痛了,还是燃不起来。到了晚上,山里气温只有七八℃,两人只能背靠着,在身上盖点树叶取暖。
地震后第三天,9月7日,甘宇收到消息:6日下午有两支武警部队徒步进来找他们了,罗永想起前一天确实有直升机进了大坝,便决定返回大坝看看,走不动的甘宇则在原地等待。临走前,罗永给甘宇摘了包野果、用安全帽兜了一帽子溪水。
花了八九个小时回到大坝,罗永没有看到救援。当时路上已经到处是滑坡,非常危险,他又饿又累,便没有再上山,挖了根半人高的竹笋,剥壳掰了一点笋尖,嚼两下,硬吞下去。大坝到处在滚石头,他捡到一只打火机但没有逗留,慢慢往附近的火草坪方向走,晚上下了雨,他靠在一棵树上休息,找不到干柴生火,又冷又困,却完全睡不着。
9月8日,罗永走到了火草坪,吃了个树上的苹果后,他用打火机点了一堆半湿的草,冒起了浓烟,坐着等了几个小时,几乎快昏睡过去时,直升机的声音渐渐逼近,他意识到自己有救了。
和罗永分开后,甘宇在原地等了三天。
有一次喝水时,山上滑坡,滚石把他左脚砸伤,他只能忍着痛走路。
担心罗永路上出意外,他决定沿着河沟,走回大坝。走到后来,他发现水淹到了大腿,过不去,往前走了一截之后,他往山上走,想去罗永之前给他指的猛虎岗。
山里雾大,看不清路,只能十一二点走,一天走两三个小时,累了找树下或岩石边,用树叶搭个窝棚,蜷缩着睡。夜里,石头“轰隆隆”垮塌的声音,伴着野兽叫声,难以入睡。下雨的时候,他把头缩进雨衣,躲在树下。好在第二天会出太阳,晒一下身上就干了。
大多数时候,没什么吃的,他饿得吐黄胆水,只能拼命喝水,喝饱。后来他找到一些掉地上的野生猕猴桃。
头几天,他能听到直升机的声音,知道是在找自己,他在树上挂衣服,隔段时间呼救一下。没有回应,让他感到难熬,只有回想一些开心的事,想家人。“纯粹是靠着信念活着,我要回家,家人在找我。”
“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找下去”
罗永获救后,甘家人才知道甘宇失联了。
9月9日,甘宇父亲甘国明从广州赶回达州老家,和妻子连夜赶往泸定,到得妥镇抗震救灾指挥部打听情况,联系搜救。
中秋节那天,工作人员给了他几个月饼,甘国明没吃。他说“我要找到我儿子才吃”。
那晚,他梦见了儿子。醒来后,他觉得“儿子一定还活着”。
10号清晨,一支16人的救援队上山搜寻了。向导是罗永堂哥,49岁的湾东村村民罗立军。他和甘宇并不相识,但他想尽一份力。
一行人先被直升机送到猛虎岗,之后徒步进山。罗永也去了。获救后,他住院没两天就出来了。脸色苍白的他一直在给救援队指路,因身体虚弱,他没有下飞机。
一路上,罗立军看到路几乎垮完了,很多地方只能绕,绕不过去,就用铁锹开路。
第一天,他们翻越了三座小山顶——其中就有最后发现甘宇的大坪。山顶上有很多牛羊和人的足迹,他们在山顶露宿,躺树叶上休息,半夜被冻醒,只好生火取暖。
第二天,他们找到了罗永和甘宇分开的地点芹菜坪,沿着地上的足迹,在附近找了几公里,大声呼喊,没有回应。
罗立军说,猛虎岗范围很大,全走完可能要一个月,在茫茫林海呼喊,即使相隔50米,可能也听不到声音,只能凭运气。到下午,救援队干粮和水消耗殆尽,只能下撤。
四天后,罗立军又带着蓝天救援队,沿另一条路线搜寻,依旧无果。
上山搜寻的还有孙建红。得知甘宇没找到,他一夜无眠。
9月9号下午,他带着由消防员、民警、志愿者组成的30多人的搜救队,从石棉方向进山。走了四五个小时,还没到猛虎岗,因为路上太危险,不具备救援条件,中途折返。
9月12号,他跟两个哥哥第二次上山,带上三天的干粮、水,还有一套给甘宇的衣服,计划把整个山找遍。
孙建红和哥哥第二次上山找甘宇。受访者供图
他们早晨五点出发,一路上,看到被山石砸坏的摩托车,坍塌的民房、猪圈,遍地跑的猪、鸡、羊,有的地方还在垮塌,只能等垮塌一停,马上冲过去,还有的悬崖边,连棵树都没有,“拿着命在走”。“整个山基本转一圈了”,林子又高又密,岔路多,他们一路在树上砍下刀印或是把竹子砍断,做标记。
出来已经天黑了。孙建红心情沉重,给甘宇妈妈发信息:“阿姨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没找到。”甘宇妈妈给他转了600元感谢,他没收。
孙建红没找到甘宇后,跟甘宇妈妈的对话。受访者供图
也是在9月12号,甘宇的两个堂哥从成都赶到石棉县王岗坪乡,寻找弟弟。他们在网上求助,联系到四支民间救援队。
每次,一有搜救队上去,甘家人就觉得有希望;一说“收队”,就悲伤。
十几天来,甘国明夫妇几乎没合眼,“衣服都没脱过”。甘国明说,他害怕找不到,又怕找到了,是不好的消息。
所有的情况都想到了:遇到野猪、熊,怎么躲?滑坡把他打倒了怎么办?泥石流把他冲到哪去了?……很快,甘国明又一一推翻所有的“不测”。
他对儿子很严,“从来没对他笑过”,儿子考第一,也没有表扬过他。甘宇失联的日子里,想起这些,甘国明感到心痛,“应该对他好一点”,“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找下去”。
最坏的情况也想过。“哪怕是一个骨头在那里,我都把他捡回去。”甘国明语气坚定,“这是我作为父亲,最后能做的事情了。”
“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孙建红后来才知道,因为对山形不熟,离开芹菜坪后,甘宇爬到最高的山的背面了,超出了救援队的搜索范围。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甘宇终于爬到了罗永说的“大草原”。天气很冷,他一晚没睡,“感觉有点挺不过来”。
第二天,天晴了。他看到有几十头牛羊,救援队员留下的压缩饼干、空矿泉水瓶,还有远处的公路。他大声呼救,没有回应。
下山的路垮了,他只能等着。待两天后,甘宇试着往下滑,找到一个平地歇了一晚。第二天,听到有人声,他大声喊“救命”。
对面山头的跃进村村民倪太高听到了,赶过来救甘宇。
被救前一晚,甘国明梦到甘宇走在老家的公路上,对他说“爸,我回来了”,之后又说“我要走了”。
“你往哪里走?”甘国明一下惊醒,一看时间,凌晨3点55分。他跟妻子说,梦见儿子回来了。
那几日,妻子也梦见甘宇在梦中喊“妈妈救我,妈妈救我”。
甘立权也连续几晚,做了相似的梦。他决心亲自上山搜寻,他找到跃进村村民倪华东当向导。
9月20号下午六点,一行人进山,打算先到倪华东家过一夜。入夜,下着毛毛雨,山路垮了,只能逆着往上爬。黑夜里,传来乌鸦“哇哇”叫、山体坍塌的“哗哗”声,还有一股腐烂的臭味,甘立权脊背发凉,忍不住想,“这么恐怖这么黑,甘宇晚上是怎么(挺)过来的?”
走了两三个小时后,到了向导家。向导家房子塌了,没水没电,只能从两三公里外背水上来。
次日清晨,他们带着帐篷、胶纸、刀、锅、米上山,计划先去芹菜坪,再翻到附近山头,找三四天。
大约两个小时后,甘立权接到了甘宇妈妈的电话,说甘宇找到了。
甘立权给倪太高打电话,甘宇接了。听到哥哥的声音,甘宇哭着说,“有家人来了真好。”
见面后,甘宇又哭了,甘立权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甘宇问他有没有肉,想吃肉。甘立权说,现在还不能吃。来的路上,石棉指挥部派来的医生在电话中嘱咐他,不要让甘宇吃东西,少喝点水,不能让他睡觉。
甘宇衣服、裤子、鞋子都湿了,甘立权给他换上新衣服。他看到弟弟膝盖磨烂了,粘住了裤子,脚腕上很多脓水,手上也伤口遍布。他衣服口袋里有一瓶路上捡的驱蚊剂。
换衣服后,甘宇依然冷得发抖。村民们砍了两根树枝,用口袋做成简易担架,七八个人轮流抬着他往山下走。雨后地上满是泥,一脚踩下去,陷进泥里,他们走50米歇会儿,不到一公里的路,走了两个小时。
下午四点多,直升机将甘宇接到了泸定县医院。
看到村民发来的甘宇的照片,甘国明激动不已,“你说哭,不叫哭;笑,不叫笑,五味杂陈,用词语形容不出来。”
在泸定县医院看到甘宇时,妻子哭到不行,而甘国明觉得,“管他断胳膊断腿的,只要人活着就行。”
被妈妈抱着,甘宇很开心,“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获救当晚,甘宇连夜转运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他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肋骨、左下肢腓骨骨折,伴有严重感染,食管、胃出现溃疡。他左侧踝关节做了手术,左脚上的钉子被取出。
甘宇在病房里度过了生日。受访者供图
10月8日,甘宇出院,回到达州老家。他想去感谢那些救助过他的人,还想去海边看看。
甘宇出院。受访者供图
甘宇觉得,自己比那些遇难者幸运得多。
“回家”
彭荣强想带哥哥回家。
他的哥哥彭云军38岁,住湾东村,两个儿子念初中,小女儿还在上小学,妻子干农活,还要照顾107岁的爷爷,日子过得很紧。
在彭荣强眼中,哥哥老实、能干,每次轮休回家,都忙着种佛手柑、养蜂、养牛。对他也很好,总帮他干活。地震前几天,他找哥哥帮忙掏蜂蜜,哥哥让等他几天。
没想到,等来的是哥哥遇难的消息。他“哭了三天”,“抱着头发扯”,两次梦到哥哥。梦里,兄弟俩像是回到儿时,在山上放牛。
彭云军妻子在地震中腿骨折,被直升机送到成都治疗,丈夫没了,她“整个人变了”。孩子们刚开始总问“爸爸哪去了”,后来知道了,变得沉默,说不出话就哭。只有彭云军母亲还不知情,他们怕她承受不住。
彭荣强最近觉得压力很大,家里房子塌了,自家有两个孩子。哥哥没了,他一个人要养九口人。
他听说,在水电站遇难的人都就地掩埋了。他想等路修好了,去大坝那儿看看,带哥哥回家。
32岁的马正军遇难了。14岁起他就辗转在工地上做小工。今年8月29日,他刚从西藏工地忙完拆架、打桩,回到湾东老家,又闲不住,9月4日,他第一次到水电站做工,搬运打堡坎用的石头,工钱170块一天。
马正军的工钱,基本用来还债,因和妻子陈芳一直没怀上孩子,他借了近11万做试管。8月,有些寡言的他还跟弟弟借了300,用来凑银行六百多的贷款利息。
他和妻子陈芳还有三个胚胎在医院,原定9月就去移植做试管婴儿。现在陈芳有些犯难,“我一个人也养不了,又赚不到钱。”
她家23亩地,去年才种的1900棵佛手柑,全因滑坡被埋了。马正军的手机,同样在地震时掩埋在废墟里,里边还记着他的还款计划:今年,他打算把跟堂哥借的2万还了。
对罗永来说,失去亲朋的痛苦更无以复加。
杨秀清说,彭云军是罗永最好的朋友,每天朝夕相处,关系特别好。罗永的事迹被报道后,有人想给他捐款,他都拒绝了,说不如捐给负担更重的彭云军家,至少自己还活着,还能挣。
但对于59岁的哥哥罗开清,罗永的愧疚已无法弥补,哥哥去水电站搬石头这份短工是他介绍的。他和哥哥感情很好,初中毕业就跟着哥哥去打工,哥哥总是找些轻活给他干,各自成家后两家也一直挨着住,平时都是互相照顾。
罗开清的儿子总劝他搬去城里一起住,但老罗更想待在老家种地。每天,他都要开视频看看孙子,这次去水电站做短工也是瞒着儿子、自己悄悄做的决定。
怕87岁父亲承受不住,罗永的家人也瞒着罗开清的事。但在安置点,有个老人跟他说,你家罗开清不在了,他一整天没吃饭,杨秀清忍着情绪,说罗开清只是脚伤了,正在成都看病呢。她还跟他说笑,“要是哥哥出事了,我们还能一天在这跟你开玩笑吗?”
罗永和父亲在临时安置点——一所小学里吃饭。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摄
没有早点把86岁的母亲从废墟里找出来安葬,成了罗永这辈子最遗憾的事,“一想起就过不得。”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对母亲忏悔,“儿子没有第一时间来到你身边。”
9月23日,确保出行安全后,罗永一家回湾东村安葬母亲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到了湾东河口,路基本垮了,他们徒步上山走了好几小时才到家。
9月23日,罗永一家走山路回湾东村时,山体留有大片滑坡印记。受访者供图
原先一栋砖混瓦房,如今只剩洗手间一堵下沉的墙立着。通过气味,他们在厨房的位置找到了她——那天她从地里掰完玉米回来,正准备做饭,地震就来了。
被埋了十八天,遗体已不成形,“只剩下骨头了”。但他们没时间哀悼,山上随时随地都可能坍塌,必须尽快下葬,墓碑也只能等之后有条件再立了。
罗永记得,地震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匆匆回了趟家,拿点母亲种的白菜和四季豆,母亲给他装了两袋,走的时候还很担心他赶夜路不安全,喊他骑慢点儿,他说要得,就走了。没想到,那会是最后一次见面。
杨秀清说,丈夫经历了这些,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守着母亲的照片流泪,晚上睡不着觉,也在哭。
9月28日,罗永给母亲和哥哥做法事开路,铃铛声与诵念声在相邻的两个帐篷间交错响起,一家人轮换跪坐在两个火盆旁烧纸钱,脸被火光灼得发红,浓烟中泛着哽咽声。罗开清的妻子迟迟未动,像望着远处,她抽了下鼻子,继续烧纸。罗明龙说,等大坝那边通路了,要把爸爸迁出来,选个好日子,找个好位置安葬。
等之后可以进湾东村了,罗永还要去帮老乡把牛羊赶出来,“但应该很多也死了”。杨秀清说,自家养了5头猪,地震后只剩3头。
“啥子都没得了,我们真是一无所有了。”杨秀清一时心酸地感叹,但转眼又安慰自己,一无所有也无所谓,只要人还在,一切都能重新开始。
罗永的家如今只剩洗手间一堵下沉的墙立着。受访者供图
梦见去世的人说他房子漏水了…
这是外婆跟我说的事情,她梦见了我外公对他说:“我房子漏水了,你们什么时来给我修修”连续梦见了几次,后来舅舅就去外公的坟前查看,发现坟上缺了一块土,棺材有一角露出来了,然后舅舅把缺的那部分用土填上以后,当天晚上外婆又梦到了外公了,不过这次是梦到外公说“房子修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梦见过外公了。果然是有些玄学在的吧。
后来有一次和同事聊天的时候我说了这件事,然后同事说她妈妈也梦见过去世的人说房子漏水了。说是梦见她外婆了,她外婆跟她妈妈说:“我的房子都漏水了,你们还不来给我修吗?”也是连续梦见了几次,一开始她妈妈没在意,但是连续做了同样的梦,她妈妈就觉得不太对,然后就回老家去了她外婆的墓前,到墓前一看发现棺木露出来了而且还坏了一角,然后找人修好以后,她妈妈就没再梦见她外婆了。
去世的人房子漏水了是不是都会这么托梦啊[捂脸][捂脸]
梦得怪异,记一下
凌晨一点多,做了个梦,觉得颇为怪异,随时记录下来。
先是梦到我的母亲,在院子里点了几处灶火(我们山区的人家,有大锅,小锅,有几处灶火也是正常的),都不是很旺,而且都是小锅灶,而且还移除了我家的大锅灶,问母亲中午吃什么饭,母亲也没有搭理我(母亲去世十七八年了[流泪][流泪][流泪])。我想烧水洗洗头,也没有点着火[捂脸],转了几圈都没有烧好水,好像觉得是阴雨天吧,家院弄得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碍事走几步都有点举步维艰[捂脸]。然后从侧方步行上楼(我们这里房子大多都有二楼,是做储物间用的,一般不住人),侧面有个小平台,平台边不高的矮墙不知被谁扒了一地。走进房子里,房子顶好好的(我们这里是瓦房,八字顶),却哗哗的全方位漏雨(原来在院子里,只是阴天,院子里有点阴湿,并没有雨,院子里还能烧火做饭),楼上的杂物都挪动了,地上积满了水,有扇窗户也开了个大口子,风雨往里面灌。心里想天晴了找人用彩钢瓦把房顶盖住,治治漏。
正在这时,听到一只老鼠在床下悉悉索索(前几天一只老鼠从窗户跑进了屋里,弄了几张粘老鼠纸想把老鼠粘住,一直没有上钩[捂脸]),一下子醒了过来。
然后查一下梦见房子漏雨什么征兆,说不,不好,有凶,说是事业不利,有人谋治你,我想我都是马上退休的人了,哪里还有什么事业。说是要出事,家人去世。这真的惊我一身冷汗,看起来这几天出门开车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而且尽量不要出门开车[捂脸][捂脸][捂脸]。更觉得父亲八十多了,非常害怕父亲有什么闪失[流泪][流泪][流泪]。查查烧火的征兆吧,倒是好事,可惜我并没有烧好灶火,母亲烧的灶火也不旺啊[捂脸]!
思来想去,翻来覆去,不得入睡[捂脸][捂脸][捂脸]
不过用科学唯物主义观点来思考自己的梦境,是睡觉前在手机头条里面看了一个江西电视台传奇故事,讲的是河南洛阳汝阳县一个离奇古怪近似乎闹鬼的故事。
毕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所以才会有这么离奇古怪的梦境[捂脸][捂脸][捂脸][流泪][流泪][流泪]
做梦梦到房子漏雨
#记录我的2023#我经常能梦到我住的房子漏雨,每次的房子还不一样,有时是独立的自建别墅,有时是单元楼,不管是什么房子都看着不结实,不是漏雨就是看到有一部分快塌了一样,以前还能梦到有很多属于我的房子一直没有收拾,导致房屋进水淤泥满地,看着都要成危房一样,但是现实中我没有这些房子,这些房子也不是我的,但梦里这些房子都是我的,而已都是时间太长久年不修的样子,谁能说说怎么回事?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06-26金火合(星盘金火合相是什么)
- 06-13八字合出伤官(八字伤官合官是什么意思)
- 06-24庚金女(庚金女是什么意思)
- 06-25三脚金蟾寓意(三足金蟾的寓意和象征)
- 06-13算命八字纸(生辰八字的纸有什么讲究)
- 06-14八字合财官(八字中的合官合财是什么)
- 06-23梦见金条(梦见金条有什么预兆)
- 06-12八字命盘寿命(八字排盘如何看寿命)
- 06-24貔貅和金蟾的区别(貔貅和金蟾有什么区别)
- 06-17八字命硬男(八字太硬的男人怎么样)
金牛座最新文章



- 12-30梦见房子漏雨(梦见房子漏雨是什么意思,周公解梦原版)
- 12-30怎么追处女座男生(如何追处女座男生?)
- 12-30旃是什么意思(堃是什么意思?)
- 12-30生于1968年(生于1968年电影)
- 12-30奔驰的拼音(奔驰的拼音怎么读音)
- 12-30香火是什么意思(手串过香火是什么意思)
- 12-30羊的守护神是什么菩萨(羊的守护神是什么菩萨 属羊人的守护神是什么 命运)
- 12-30企业名称怎么取(企业名称怎么取免费)
- 12-30属鼠今年几岁(属鼠今年几岁2023)
- 12-30简单窗花的剪法步骤图幼儿(剪简单窗花的详细步骤)